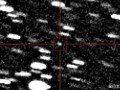8月11日,医药代表陈曦坐在宝山区某医院门诊大厅,紧盯诊室门口。
入行三天以来,她没敢敲眼前的门。身边不时有保安巡逻,她牢记经理嘱咐,病历本要一直握在手里,特殊时期千万别“顶风作案”,不然很容易被保安架走。一切合规拜访,“等风头过了再说。”

2023年7月21日,“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视频会议”召开。全领域、全链条、全覆盖的医药反腐风暴就此开启,为期一年。
一时间,医药销售成为重点打击对象。拜访业务、学术会议、行业活动纷纷暂停,许多从业者休假、转岗、转行。焦虑的医药代表们涌向社交媒体,写下“行业大变天”“医药销售圈人人自危”“代表何去何从”……
这并非医药领域第一次反腐行动,却是整治力度前所未有的一次。
当行业走过“野蛮生长”,无序的一面正在风暴下显露。
“神经末梢”
“我们就像毛细血管,处在医药系统的神经末梢。” 董冉曾做过10多年的医药代表,如今在一家药企的市场部工作。
她说,医药代表数量大,却是医疗组织架构里最弱势的群体,在行业 “阵痛”中反应最强烈。
反腐以来,她眼见销售圈里的同行“被迫休假”。不少代表调侃,朋友圈不是在外旅游,就是兼职干起卖玉石、美妆等行当。
陈曦还在岗位上,工作任务却从拜访变成“打卡”:每天跑两到三家医院,进出各拍一次照上传钉钉。“进医院和做贼一样心虚,难道以后都得这样?”作为新人,她没有任何客户资源,这个月没业绩的话,到手只有5800元的税前工资。经理承诺,等过阵子带她去见客户,现在“保命要紧”。
上海汇业律师事务所郭亚飞律师指出,此次医药反腐力度空前,将会明显加大对行贿端的刑事追责力度。多省的集中整治举报对象中,“医药代表”赫然在列。
此前董冉的抖音账号,分享过不少医药代表的日常。8月起,这些视频底下不断有网友留言:“女代表是不是都靠那种交易?”“代表就是送钱。”“找个正经点的工作吧!”
她感到委屈:曾经,医药代表有过体面的形象。
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,外资药企涌入中国,国内第一次出现“医药代表”,属于医药企业销售部门。2015年,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将医药代表定义为“从事药品信息传递、沟通、反馈的专业人员”。可以在合规的前提下,拜访医院医生。
2000年,药学毕业的董冉通过朋友介绍,进入世界500强的某外资药企,成为一名医药代表。
董冉记得,公司管理很严格。“每个代表都要经过15天的封闭培训,衣服必须有领子和袖子,裙子的长度不能在膝盖之上,连每天背包里要放哪些资料,都是规定好的。”
当时,董冉每个月有8000到9000元收入,每年有固定的加薪,出差时住的酒店几乎都是五星级。她看起来,比很多在医院、药店的老同学“光鲜”。
但同时,她眼见医药行业里,个人代理商的数量庞大。
一位药企管理者表示,90年代起,药品生产厂家便开始找代理商负责药品销售,主要出于节约时间、人力成本、合理避税的考虑。代理商从一级到多级,由省市向地区层层下放。这些从业者赚取药品成本和销售额之间的差价,被业内称作“大包”或“外包”。
“现在所说的300万医药代表,应该是把这些代理商都算在内。”董冉认为,代理商的从业人员和传统医药代表相比,专业性和收入难以保证,鱼龙混杂。“他们如果没有客户关系和资源,根本拿不到产品。”由此,一些不合规的拜访、销售行为开始出现。
“神经末梢的反应,只是大家看到的表面现象。”董冉说。代表们的“震动”背后,是行业长期的“野蛮生长”。
竞争入院
曾在罕见病药企工作的余珺看到,药品从一个理论、一个靶点最终成功上市,平均是10年,其间需要多轮融资。钱是医药研发的“生命”。
但一款药物的专利期限是20年,从研发开始算起,申请上市还要12到18个月。很多药品上市时,专利期只剩两到三年。专利一过,就会有大量仿制药出现。因此,大部分药品需要在有限的时间里,竞争入院的机会,以抢占更大的市场份额。
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研究员傅虹桥表示,目前80%左右的药物品类仍在集采(国家统一采购药品)之外。
前医药代表黎晖谈到,集采之外的药物入院门槛较高,需要经过临时采购、主任提单、开药事会表决、院长签字等。那么对于药企来说,就要“打点”其中一些关键的权力人物。“除了主任,药企基本会把药事会成员都走一遍,一些药企直接让主任去做成员工作,避免直接接触。”他说,不同医院的药事会周期不同,药品进院最快是两到三个月,“打点”工作需要从临时采购前就提早准备。“打点”的操作很多,最直接的就是送钱。
“如果不要钱就能谈下来,干嘛要花钱?无非是市场太难做了。”董冉表示,进院难一方面是药品“不好”或“可用可不用”,大部分医生是有良心、冷静的,不会选择这样的产品;另一方面是产品同质化严重。同类药品要做差异化,评判指标首先是疗效、安全性,然后是价格和客情关系。
余珺负责过一款罕见病创新药的销售,需要代表去向医院普及药物。“十万个人里只有一个患病的,根本赚不到钱,人家凭什么用?”她苦笑,一个医生留给医药代表的时间往往只有两到三分钟。如果对方看不到药品的“痛点”,代表根本没机会介绍临床数据。
在黎晖看来,药品市场很“卷”,特别是心血管、骨科和慢性病药物。就拿治疗肿瘤的PD-1药物来说,截至今年2月已有100多家企业涉足研发。
不过,余珺和黎晖都谈到,目前医药市场仍以仿制药为主,真正的创新药很少。现有的创新大多是对已有的药物进行修改,或对老药提纯,没有“独一无二”的竞争力。
“我要在同质化的药品中去找细微的优点,不断扩大、扩大。”黎晖说道,因此申请入院的过程中不免有恶性竞争:打低价战、提高回扣、举报对手“使绊子”等等。
同时他提及,集采范围内和已经进院的药品也会寻找增量市场。这些药物的价格被压得较低,需要“走量”获取更高利润。
全国某综合性医院的医生江皓透露,早期,一些医药代表会找科室主任谈回扣。在他所在的医院,回扣一般在药物价格的10%到20%之间,再由科室主任分配给手下的医生。“他们会找信息科统方(调出每位医生的开药数量),以此为依据算钱。”
天价销售
在一张2022年上市医药公司的支出清单中,销售费用超过50亿元的公司有10家,超过10亿元的有89家。其中,最高的销售费用达到91.71亿元。
黎晖指出,“天价销售”一是用于医院回扣等利益输送,二则是举办各类推广活动,最典型的是学术会议。“同时销售也是个‘万金油’,很多未知的支出都被包装成销售费。”
余珺表示,药物刚上市时没有名声和口碑,根据法律规定,不能直接向患者做广告,只能通过学术会议“隐性推广”。
“来讲课的都是专业大咖,对台下的医学人士很有影响力。”她说,药企的市场部会为专家“编好故事”:设计部分讲稿或幻灯片内容,介绍企业新推出的药物。“内容都是事实,只不过是有利的事实。”
她谈到,学术会议需要大量赞助,比如每一年度的乳腺癌大会需要50到80万元,招商明码标价。其中一个小展台的价位大约是5万元,茶歇的广告位是10万元。一场学术会议还会有许多“卫星会”,大家在大会场听完之后,再到其他的小会场举办论坛、沙龙。这些费用,由一家或多家企业赞助。
对于备受争议的专家“讲课费”,董冉强调行业内有“321”的支付标准:按医生的职称等级划分为3000元、2000元、1000元。“如果是院士或顶级的老师,可能会增至5000元,8000元到顶了。这是同类公司都默认的事。”
“一些小公司没有名气,会疯抢一个展台的推广位。”一位医药代表曾见过,原先教授的讲课费是3000元,但不少公司恶意哄抬价格,“有人突然喊出一万元,很快就会有两万、三万元的跟上。”
对此,上海市律师协会医药健康业务研究委员会主任卢意光表示,判断学术会议是否合规的标准一是“定性”,有些是假会议,根本没开,或者就是打着学术幌子做广告宣传,专家成了药企的“广告代言人”。二是“定量”:医药企业支付给专家的报酬是多少?比如2000到5000元是合理的,但他曾碰到过极端的案例,一堂课下来教授的讲课费高达5万元。
“一些药企的利润,50%以上,甚至80%、90%都用来做营销、做推广。这些费用应该用以开发新药。”卢意光直指,长期以来,很多人会指责“我们的药品安全无效,费用高”。如果不扭转营销至上的氛围,药企会陷入重推广、轻研发、药物难以创新、不得不加大推广力度的“恶性循环”。
余珺却感到无奈:很多有医学前景的研发项目,因为没有打动人的“故事”,难以打开市场,“投资人精得很,自然不愿意投”。由此,企业没钱用以研发,研发失败后亏损更多的钱,直至倒下。“再高尚的科学,也需要钱养着。”
2022年初,余珺所在的药企因为利润下降,没有融资,辞退了三百多位员工。45岁的余珺是其中之一。
合规之路
卢意光曾是一位外科医生。他看到,2000年前后,市场化改革鼓励医院创收,允许药品加成。“以药养医”的背景下,催生了看病贵、看病难等许多矛盾。
江皓工作已有30余年,他描述,当时是医药代表“最猖獗”的时候:一些医生治疗时,有医药代表就坐在一旁数数,一天下来开了多少支药,直接当天结算;一些医生刚做完手术,门口就会有代表准备好的小吃、饮料。
“比我大的主任和前辈都在拿,我为什么不拿呢?”他坦言:“不拿的话,很怕被孤立。”
卢意光说道,早期,年轻的医生受到整体环境影响,会觉得拿回扣是件很正常的事,长此以往助推了医药行业“劣币驱逐良币”的风气。
但董冉观察到,2000年以来,很多药企开始开展合规工作。以她所在的企业来说,每个月老板会给到每位医药代表最多三节科室会(代表去医院科室的产品宣讲会)的预算,3000元左右,其他费用是没有的。代表在科室会后,需要向公司提交相关的证明材料:时间、地点、任务内容。“每个月我都要花大量时间,把材料做成一本书。”
在卢意光眼中,合规之路真正启步,是在2009年“新医改”之后:全国范围内逐步取消药物加成;推行“两票制”,在药厂到医院的药品流通环节只能开两张发票,减少层层盘剥;各地开展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等。“以药养医”的时代渐渐落幕。
而让董冉切身感受到合规趋势的,是2014年,跨国药企巨头葛兰素史克因行贿受贿案,被开出30亿罚单。这一年,多家药企频频被罚,医药行业出现了“跳槽潮”,越来越多的从业者开始在就业时重视合规政策。
近年来,江皓所在的全国某综合性三甲医院,已经对临床医生用药有严格的制度规范:医生一旦被发现开药的用量、次数或适应症不对,每一例的罚款是药物的原价。如果是重大过错,每发现一例的罚款正从二三百元上升到一两万元。“乱开药的话,倒扣的钱比回扣挣的多,还会被医院谈话。”
今年年初,黎晖感受到合规趋势愈演愈烈,他决定离开销售岗位,做一名药企合规咨询。
在他看来,医药行业的合规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”。
“现在多数企业追求的仍然是财政或刑事合规,也就是给各类灰色、行贿行为穿合规马甲。”他说,很多医药企业仍没有做到业务和行为合规:通过学术会议的不正当竞争影响医疗从业者的处方行为,利益输送通过互联网医疗等手段,更加隐蔽。
另外,他谈到一些药企没有专门的合规部门,合规内控业务由会计、财务负责;很多医院也没有健全的、地区化的拜访制度,医药代表进院开展活动,“规则并不清晰”。
“短期来看,合规会给企业带来较高的成本,但这是一笔长远的投资,未来对违法成本的拦截是非常有效的。”他说。
等候回归
2016年,刚从医药大学毕业的黎晖,觉得自己的专业崇高、圣洁,笃定了此后从事医药行业的人生方向。
但七年来,他觉得医药变成一个产品、一行利润率、一个浮动的数字,和上学时“治病救人”的理想渐行渐远。
“理想和利益之间,还是要找到一个平衡点。”他指出,医药企业需要盈利,但行业里也需要一些纯粹的研究人员去推动技术发展,需要一些更公平的规则和保持中立性的机构存在。
傅虹桥和卢意光都提到,医疗改革不是一朝一夕之事,和其他行业不同,医药、医疗行业的监管涉专业性要求很高,本身落地就有许多难题。先要“纠正一些明显不对的地方”,再去推动更加专业的改革、理顺行业秩序,公立医疗机构最终要回归公益性,医药行业要倒逼企业真正靠创新能力发展。“这是一个很长期的愿景。”
在董冉和黎晖眼中,短期内,医药从业者可能会陷入低谷,但身处风暴,“是挑战更是机会。”
董冉认为,随着行业的改革,医药代表的数量会减少,但门槛和含金量会更高。她了解到,在全球,一些优秀的医药代表有更高的学术能力,能够向医生介绍行业前沿知识、收集医院临床数据、将医生的创新想法传达给医药企业,成为药品创新向商业运转的重要一环。“希望有一天,医药销售能以正面的形象出现在大众面前,出现在杂志封面,成为一类人的代表。”
黎晖最近频频在社交媒体上科普医药企业的合规知识。不少企业来找他咨询,希望能在这段休整的时间里,主动去琢磨一些合规政策和方法,在公司里建立起合规部门,重新部署人员。
余珺面试了好几家医药公司。她仍觉得,医药是一个有影响力的行业。药品技术的一小步,或许能延续一段高质量的生命,这和普通的销售完全不同。
傅虹桥说,医药反腐或许是一个很好的契机,去推动更长效的制度化改革:提高医生的待遇和公众形象。目前腐败集中在“关键少数”,占据多数的一线医生,应该有更合理的薪酬制度和福利体系,让他们的回报体现付出的价值。
董冉说道,曾经夜访医院时,很多医生都会赶回来,查看病人的病情,再回到办公室加班。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颇有名声,仍在提升自己。
“那些时刻,给了我向前的能量。”董冉记忆犹新,夜晚11点,每一扇开灯的窗户,点亮了一座医院大楼。